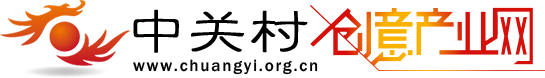通知公告:
 首页 » 产业发展 » 产业动态 » 其他
首页 » 产业发展 » 产业动态 » 其他
展望2021游戏直播:利益攸关者需合力打造共赢生态圈
近年来,网络游戏直播作为新兴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参与,在吸引大量玩家的同时,侵权风险日益显现。此前,发生在游戏直播领域的侵权事件并不少见。
网络游戏直播到底侵犯了游戏版权人的何种权利?网络游戏直播者(包括平台方和主播)应当采取何种版权使用方案才能规避侵权风险?既有的司法裁判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21年,新修《著作权法》将开始实施,其中对合理使用等条款的修订,以及对广播权等权能的扩充,必将促使网络游戏直播行业迎来新一轮大洗牌。
展望2021年,网络游戏直播行业利益攸关者需要在版权许可方案调适、合理使用条款的精准把握以及商业模式的优化调整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研判,以期促成新型高效优质的交易惯例,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网络游戏直播产业生态圈。
网络游戏直播的法律性质有待明确
由于网络游戏的独立作品地位并未在新修《著作权法》中得到确认,故只能基于某部游戏自身包含的内容要素予以个案判断。根据美国学者阿什利·桑德斯·利普森和罗伯特·D·布雷恩的界定,电子游戏由三类元素组合而成:音频元素(包括音乐、录音、语音、植入音效、内在音效)、视频元素(包括摄影图像、数字捕获移动图像、动画、文档)、软件代码(包括主引擎、辅助代码、插件、执行命令)。网络游戏作品的独创性体现于上述三要素的组合之中或独立要素自身之上。
既然网络游戏的整体(要素组合)或部分(独立要素)都可能含有创作性成分,因此不论是驱动处于底层的软件程序,还是对操作游戏呈现出来的连续动态画面予以直播,都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使用行为。前者涉及网络游戏软件程序的复制,后者则是对网络游戏视听要素的公开表演。
在不同的法域,对游戏直播这种行为的界定仅仅只是法律术语的区别。例如,在欧盟,这种行为落入公开传播权的规制范围,而在美国则涉嫌侵犯表演权。笔者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的框架下,这种行为同样受表演权规范。一般而言,没有事先获得授权或者具备法定的侵权抗辩事由,对操作游戏所呈现画面的直播构成版权侵权。
是否构成合理使用需依据个案判断
网络游戏区别于电影、电视、音乐等其他娱乐媒体,其本质特征是互动性。其他娱乐媒体具有单向输出和单向接受的被动性特征,但“玩游戏”是一种双向互动型娱乐,而对操作游戏形成的连续画面进行直播则不具备这种特征。观看游戏直播的消费者并不会因为欣赏直播而替代自己亲自操作游戏的娱乐活动。相反,一些本来不消费游戏的消费者可能因为观看游戏直播而对其产生兴趣,进而产生实际操作消费交易。用经济学术语界定,观看游戏直播并不是玩游戏的竞争性替代品,而是一种增益型互补品。同时,游戏直播往往并非游戏画面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再创作或新型使用,使原游戏画面具有了此前不具备的新价值和意义,构成转化性使用。
业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业性使用与合理使用是二元对立的存在。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即便在版权保护程度较高的美国,也不排除一些商业性使用构成合理使用,关键在于是否符合版权合理使用的四项标准:使用作品的目的及性质、版权作品的性质、版权作品的使用数量及质量、使用作品对作品的价值或潜在市场的影响。越是程度高的商业性使用越不可能构成合理使用,越是转化性使用程度高的建设性使用则越可能构成合理使用。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商业性使用均不构成合理使用;同样,并非所有的转化性使用都一律构成合理使用,关键在于根据个案情形进行有针对性地判断。
笔者认为,只要在今后网络游戏直播转化性使用程度较高,且使用的量限定在引用原作达成批评、评论或介绍某款游戏技法、战果或游戏商品客观属性的必要限度之内,则此种游戏直播构成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就非常高。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直播的重点是与观赏者进行互动交流且游戏解说展现了高度的模仿讽刺性表达和其他创造性表达,此时所直播的网络游戏仅仅是互动者维系社群关系的纽带,只要使用的量适宜,则这种直播亦得以构成合理使用。
如何达成利益平衡是发展关键
现在,知名的网络游戏开发方倾向于禁止未经授权的游戏直播,而新出道方则希望更多的直播者免费直播其游戏,提高其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同时,不同的直播者基于不同的网络游戏所展现的再创作高度也缺乏同质性。这样,任何整齐划一的“一刀切”规制模式必然有利有弊。
新修《著作权法》在合理使用制度原则条款中引入了《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测试法”,在免费表演条款中加入了“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刚性规定,将合理使用的门槛设置得更高。
直播者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开展直播业务,仅仅寄希望于合理使用条款的庇护,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侵权诉讼的高度风险之中。这样,版权侵权风险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意图进入网络游戏直播行业谋生的从业者畏葸不前,而本可因这一产业的兴盛而充足供给直播再创作的市场也因高压侵权的“寒蝉效应”而萎缩。即便如任天堂公司采取的合作分成模式(只要直播其网络游戏者分享广告利润,就允许他们直播其游戏)也非包医百病的万能灵药。
直播网络游戏落入著作权之排他权的控制范围,将这一控制权交由版权人掌握,会因其实施许可而获得相应收益,也能使其合理微调进入该网络游戏直播市场的许可数量,这可能不会彻底阻碍游戏直播产业的市场培育与发展。但这种单一措施也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
如若给予网络游戏版权人更强的控制权和更多的经济价值获取权,则意味着再创作者更加萎缩的创作空间和更少的创作收入。与此相应的是,再创作作品的更少数量和更差质量的市场供给。这取决于许可者和被许可者实施或获取许可的交易成本考量。像任天堂这种“通用型”解决方案固然会抑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直播者直播其游戏,但个性化的许可方案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繁冗举措。
因此,如何在游戏版权拥有者和直播者,以及希望享受更多优质游戏直播视频服务的公众之间达成合理的利益平衡,将是未来产业利益攸关方亟须解决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